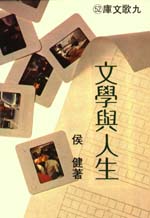
侯健開頭便寫民國以來的文學思想運動,便是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和其後的革命文學,且點出兩者基本精神上並無不同,皆把文學本身做為社會改革或政治變更的工具。侯健並引哥德的批評話語:「任何革命,都無法避免趨於極端。」(頁204)為中國這兩場革命定下揚棄傳統的命運。文學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,而革命文學則成了無法遏止的思想混淆、動盪。侯健以白璧德(Irving Babbitt,1865-1933)的文學觀看待這兩次所謂的「革命」,白璧德強調文學毋需教條主義,而是要以傳統為依據教育完美的人。因此侯健認為文學革命是深具破壞性的,因為文學革命抹煞了固有傳統,而革命文學更不用說,其基本精神仍承自文學革命,並對思想更肆無忌憚地展開破壞。
〈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〉一文也對這兩場革命運動的性質,做了些許釐清。首先就文學革命運動如何起頭作一梳理,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大都認為是由陳獨秀辦的《新青年》雜誌率先發難的,然而侯健於此以魯迅為旁例澄清,他寫道:「據後來並非『我的朋友』魯迅說,他注意到新青年,便是由于這篇文章,因而他為『新青年』寫『狂人日記』,寫『雜感』,從而開始他在白話文學上的『事業』,都與胡適直接有關。」(頁207)魯迅所注意到的文章便是胡適1917年發表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,可見胡適〈芻議〉將文學革命帶至公共性質的另一層次討論。但實質上,侯健卻把文學革命具體的作為功效歸諸於周作人〈人的文學〉(1918年12月),周作人提出文學應以人為主的主張,要排除的是阻礙人性的封建禮法,是一浪漫主義的人道思想,也正符合胡適所提倡破壞的,反傳統的個人主義精神之革命內涵(走向人的自由解放),而魯迅1918年5月發表在《新青年》的〈狂人日記〉亦是這種精神的第一聲呼喊。魯迅1926年於黃埔軍校演講「革命與文學」,他認為革命前後可以有文學,但實際從事革命的時期則不能有文學。魯迅〈革命文學〉指出:「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: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,斥駡他的敵手的;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“打,打”,“殺,殺”,或“血,血”的。」以上魯迅所謂的「革命文學」是反文學的,由此可見魯迅認為應把革命的觀念性統一至文學,重視精神層面。魯迅一反當時的革命文學為口號、教條服務的說法,且其與梁實秋的論戰同時證明他的浪漫性格,這性子正連接上五四前後文學革命的個人主義味道。
而魯迅究竟是為何加入「左聯」?為何「轉向」?雖很模糊,但侯健也試圖在文中作一解釋,其一便是共產黨的攏絡,其次是魯迅好友馮雪峰及左聯成員的拉攏。但就魯迅因無處發表文章而轉向這一個說法,侯健提出確切的辯駁(當時仍有《語絲》、《大眾文藝》、《奔流》及甘人、林語堂等力量助威,詳參正文頁226~226)。二○年代末魯迅面對革命文學多次指出要害,他主張文學反抗正在暴露黑暗面的貢獻,於反抗過程中放出光明。但是當時革命文學家的革命卻是對暴露黑暗的否定,這已很清楚地悖離魯迅對「革命」的意義。然而隻身魯迅豈能抵擋千軍萬馬的革命文學風潮,難怪侯健文末也大嘆民國以來的兩次文學運動:「不幸的是,它們都是成功的。」(頁227)說到底自五四文學革命至其後二、三○年代革命文學的發展,也僅是一場人文/浪漫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延伸。
作者介紹:
侯健 (1926年07月~1990年08月)
號建人,山東人,民國十五年生,臺大外文系畢業,賓夕凡尼亞大學碩士,石溪紐約州立大學哲學博士,歷任臺大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、系所主任等,現兼文學院院長,曾主編學生英語文摘、文學雜誌、中外文學等。著有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、二十世紀文學、文學思想書;譯有柏拉圖理想國,英文著作多篇未結集。
參考書籍:侯健,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》,台北:中外文學月刊社,1974。
原文載於《文藝復興月刊》41期62年5月,後轉刊於侯健著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》附錄一。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